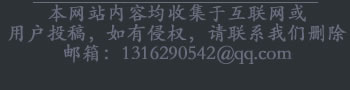首页 > 最新信息 / 正文
:文学数理批评(4).jpg)
:文学数理批评(4).jpg)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文化、哲学的基本精神[]。作为对世界存在与运动方式的基本认识,它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和思维表达方式,从而论事为文都注重“究天人之际”(司马迁《报任安书》),也就是寻求“天人合一”的境界。这一点对中国古代小说创作总体构思和情节布局的影响之大,远过于其他任何个别的观念和方法,却从来很少人谈到过。
这个问题所以很少研究,大约是因为“天人合一”思想与小说的结构看起来关系太过遥远。其实,小说结构说到底是作者心目中现实世界存在与运动方式的文学显现,它体现的是带有作者个人特征的人类对世界构造的一般理解。所以,作为中国古人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天人合一”自然成为小说构思布局的指导思想,从而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结构艺术。
如同一切伟大的思想,“天人合一”具有被永久阐释的可能性。今人对它的解释,多强调其人与自然和谐的合乎现代科学走向的一面。其实,中国古代所谓“天人合一”,特别是汉代以后对小说影响日渐深入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一种带有浓厚神学色彩的哲学观念。它的内涵各家说法虽有不同,而实质都不过是在“唯天为大”(《论语·泰伯》)的前提下讲天——人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大约有两个要点,一是天人同构,人为取法天道;二是天人感应,天命支配人事。它肯定了天——人的谐和与互动,却带有神秘主义和机械比附的缺陷,从而给古代小说构思布局的影响,往往是造成某些世代沿用的结构模式。
所谓天人同构,是说天人同类,人副天数、合天象。这个思想虽然晚至汉儒董仲舒才最后形成系统的理论[],却早在先秦就已酝酿发生。《吕氏春秋·有始览·有始》:“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大同”就是相类, 高诱注:“以一人身喻天地万物。《易》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故曰‘大同’也。”即“一人之身”类同“天地万物”,也就是“人”与“天”同构。故天之道即人之道,人为应该并且只能取法于天道。《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包含天道是人为根本法则的道理。而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系辞上》)“象之”,就是模拟天道以成人文。《礼记·礼运篇》也说:“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郑玄注:“天地以至于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韩非子·扬权》曰:“若地若天,孰疏孰亲。能象天地,是谓圣人。”《吕氏春秋·圜道》云:“天道圜,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总之,儒、道、法家等对“人为”的观念虽有很大或根本的不同,但肯定人为取法天道一点完全一致,从而共同奠定中国人法天行事的传统观念。
同时,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学认为,天道有“象”有“数”,《易传·系辞上》:“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这就是说,人为取法天道,“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易传·系辞上》),其具体操作是“错综其数”以成“文”,“极其数”以定“象”。可以说,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就是这样被确定下来的。世人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从华夏民族的象形文字、“天子”以下的政治制度到世俗礼节仪式、音乐舞蹈,从明堂、辟雍、天坛、地坛等建筑到辇车、古币的造型,世间无处不是合天数、肖天象的制作,而作为古代保存和传播文化基本载体的书籍的编纂自然也不能例外。《易传·系辞上》曰:“《易》与天地准。”又曰:“与天地相似。”就是说《易》法天地以成文。而所谓“圣人设卦观象”,“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就是说《周易》八卦为宇宙最简的模型。这个例子也许太过费解,但是我们看《周礼》的六官(天、地、春、夏、秋、冬),就更容易知道古之作者法天地四时以为全书结构的用心。他如先秦古史多以《春秋》命名,也是取象于四时。《吕氏春秋》“事之伦类与孔子所修《春秋》相附近焉”(孔颖达疏),所以也名曰“春秋”。并且它的十二纪,以次以一年四季十二个月令为题,以其天象、物候领起,为编排之序,更显得象是一部标准的“天书”;再如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说明作《史记》三十“世家”的根据:“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而据研究者认为,《史记》十二本纪拟十二辰,十表拟天之十干,八书拟地之八方,也是按“天”之象数建构的。这种取法天数、天象以为著作体式的传统延伸至小说的构思布局并积淀为一定的模式,乃是中国人思维和表达方式自然趋向。
首先,是法天之“数”。中国古代小说构思布局很注重“错综其数”和“极其数”,以成全书之“文”、定全书之“象”。这类表现可见于大大小小的许多方面。大略而言,中国古代小说在构造故事、布局全书上用数字最多,无论分卷、分回、记人、记事、记物、纪时、纪程,都往往有明确的数字。其数量之大,地位之突出,只要与西方古典小说稍加对比,就可以看得出来。例如《水浒传》开篇“诗曰”以后“话说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点,天子驾坐紫宸殿”云云,如此设时的叙述,在西方小说中是决难见到的;而“一百单八将”“十二金钗”“百花仙子”等成群结队的人物设置,在西方小说家也难以想像。夸张一点说,中国古代小说在构思布局上有近乎“数字化存在”的特点。这一特点更为突出地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结卷尚偶数,通俗小说尚“10n”之数。关于结卷尚偶,只需浏览《中国文言小说书目》(袁行霈、侯忠义编)和《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编)二书的著录即可知道:在古代所有几千种小说书中,除不分卷或只有一卷(实际也是不分卷)者外,很少以奇数结卷的。如果说文言小说中还有些分为三卷、五卷的书例,则在通俗小说中就极少见到了。这就是说,中国古代小说大致遵循了以偶数结卷的原则,无论分卷分回(则),其组织结构都以偶数也就是2n之数为尚。这不限于小说,从清代的金和跋《儒林外史》称“先生著书皆奇数,是书原本仅五十五回”云云逆想可知,古人著述有约定俗成以偶数结卷的传统,小说结卷尚偶数只是这一大传统的表现。其根源应在于古人对数字“二”的认识。《易传·系辞上》:“一阴一阳之为道。”即二偶为道;宋儒蔡元定曰:“数始于一奇,象成于二偶。”(《宋史·蔡元定传》)即二偶成象。古称命运多舛为“数奇”,今俗云“好事成双”,反映的都是中国人尚偶数的传统。所以古人著书以偶数结卷之习,就根源于数字“二”有“为道”和成“象”的象征意义,形成于以“成双”为好的民族心理,从而一部书只有以偶数结卷才算结构圆满。
但是,作为结构圆满的标志,各个偶数象征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几乎是千篇一律以偶数结卷的古代通俗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以若干个十回即“10n”为度的情况较为普遍;而在代表了中国古代小说最高成就的长篇名著中,以百回结卷者占了一个颇大的数量。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除却作品内容客观需要的大致长度之外,还应当是由于古人传统上对数字“十”的特殊认识。《易·屯》:“十年乃字。”孔颖达注曰:“十者,数之极。” 又,《说文》曰:“十,数之具也。─为东西,〡为南北,则四方中央备矣。” 又,《史记·律例书》:“数始于一,终于十。”因此,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十”有全备终极之义,成语“十全十美”生动地反映了华夏民族以“十”为圆满的心理共识,其偏至乃形成日常生活中的非“十”不为满足的“十景病”。而从《战国策》述苏秦说秦“书十上而说不成”、陶潜《闲情赋》的“十愿”到《水浒传》写王婆的“十分挨光计”,我们也可以看到古人属辞述事以“十”为法的一线传统。同时,正是在《水浒传》的说话中,有“林(冲)十回”“宋(江)十回”“武(松)十回”等以“十回”为小说叙事单元的现象。所以,古代通俗小说的“10n”结卷度数,特别是以《水浒传》打头,《金瓶梅》《西游记》《封神演义》《三宝太监西洋记》《隋唐演义》《女仙外史》《醒世姻缘传》等等“百回”结卷模式的文化心理依据,应是“十”之倍数,特别是“百”作为“十”的十倍之数,比其他任何偶数更具有象征圆满的意义,它们是建立在传统取法天数、以“十”为全、以“十”为美的文化心理之上的。
(二)“三复情节”和“三极建构”。中国古代小说以“数”定“象”,更多地用到数字“三”。关于古代尚“三”观念的产生和“三复情节”,笔者已撰文有所说明[],兹不复述 。但是,“三复情节”体现的是时序上尚“三”的观念,而古人在空间关系上也同样有尚“三”的传统,并影响于小说的构思与布局,还需要有补充的说明。
空间关系上尚“三”意识的形成,除源于《易》学“三才(天、地、人)”思想,大约还受了上古科学知识萌芽的影响。古代天文学以日、月、星为“三光”,《说文》释“示”字为“天垂象”,以“二”下的部分为“日、月、星”之象征,这个认识可以加强空间位置上“三”的意义。而相传大禹铸鼎,三足两耳——鼎用三足,所谓“三足鼎立”的三角形稳定性的事实,同样可以加强空间关系上尚“三”的意识,并渗透作用于社会生活。
古人空间关系上尚“三”的观念应用于人事,大约最先表现于战争。早在商周时期军队的编制,一辆战车上甲士三人按右、中、左成“品”字形布列;全军也按右、中、左三分制,以便于用兵布成“品” 字形(古人称“三才阵”,今人称“前三角”)或倒“品”字形(古人称“鱼丽阵”,今人称“后三角”)阵势[]。在政治制度上,周朝和汉、唐天子以下最高长官为三公,南北朝以后又形成三省制。所以设三公、三省,应当是由于三者并且只有三者并立的设置才最便于折中决事和相互制衡。其运作原理,在现代军事、政治中也还可以看到它的应用[],但早在《淮南子·说林训》和《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都曾出现的兔死狗烹的比喻中,已经可以见到这一认识的萌芽,而《史记·淮阴侯列传》载武涉说韩信一段话,讲得更为明白:
“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以项王存也。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项王今日亡,则次取足下。足下与项王有故,何不反汉与楚连和,参分天下王之?今释此时,而自必于汉以击楚,且为智者固若此乎?”
蒯通也对韩信表示过大致相同的看法:
“当今两主之命县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诚 能听臣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参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
而韩信不听。后遭云梦之祸,韩信始悔不当初,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这些议论和韩信最后被害于长乐钟室的结局,从正、反两面体现了人事运作通于几何学上“三点成面”(即经过不在一条直线上的任意三点,可以作一个平面,并且只能作一个平面)和三角形(不在同一直线上的三点间的线段围成的封闭图形)稳定性的原理。它传达了中国先民早就意识到“势不两立”“三足鼎立”等人事制衡通于天道的历史信息。这一认识要在古代小说的构思中体现出来,是顺理成章的。
“鼎足而居”的三者从几何学的观念看是三角形的三个顶点。因此,笔者把这种与空间关系上尚“三”观念密切相关的“三足鼎立”式的小说结构现象称之为“三极建构”。
“三极建构”由三方“鼎立”而成,三方互动又互为制衡。其状态有三种样式:一是三方循环相生,如《三国演义》中刘、关、张三者的关系,他们结义的誓言“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是三者循环相生(实际是共生)的说明;二是三方循环相克,如《三国演义》“入西川二士争功”,写邓艾反司马氏,司马昭令钟会收邓艾,又以钟会“后必反”,自己统兵于后收钟会,成循环制胜态势;三是两方相克或相生,第三方居参与地位。两方相克,第三方居参与地位的,如《三国演义》写魏、蜀、吴之争;两方相生,第三方居参与地位的,则如才子佳人小说中的才子、佳人、(其间拨乱的)小人,等等。
第三种情况的“三极建构”在古代小说中最有意义。我们先来看《三国演义》的例子。此书写三国之事,蜀、魏作为对立的两极构成全书叙事主线,吴国作为主构之外的第三极,成为蜀、魏之争的牵制因素。这种互动又互相制衡的三角态势在《三国演义》艺术结构上的优越性是明显的,章培恒等《中国文学史》说它:“由三方鼎立而彼此间组合分化、勾心斗角所形成的关系,较之双方对峙(如南北朝)或多方混战(如战国),有一种恰到好处的复杂性,能够充分而又清楚地显现政治作为利益斗争的手段的实际情状。”[]但是,罗贯中首先意识到的并不是这种结构上的好处,而是这一“鼎立”态势顺应了“天人合一”,《定三分隆中决策》有如下描写:
(诸葛亮)言罢,命童子取出画一轴,挂于中堂,指谓玄德曰:“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图也。将军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以成鼎足之势, 然后可图中原也。”
这可以看作“鼎足之势”即“三极建构”上升到的“天人之际”的说明,实际就是把“ 三国演义”的故事构架定位在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对立和依存。联系《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七《刘玄德三顾茅庐》写崔州平论世道治乱相仍、“如阴阳消长,寒暑往来之理”一段话,认为罗贯中自觉地把“天人合一”作为《三国演义》布局的指导思想,应当是合乎实际的。《水浒传》写宋江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总体构思——梁山好汉、贪官、皇帝的鼎峙关系也暗合了“三极建构”的原理,就不细说了。
我们再来看才子佳人小说的例子。这类小说布局的一般情况是:在作为故事主构的两极相生的才子与佳人之外,总有一个作为情节中介的第三者,即曹雪芹于《 红楼梦》第一回所说“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虽然对才子佳人小说的造作颇致不满,但他的《红楼梦》其实还是暗用了才子佳人小说中已成腐朽的“三极建构”,只是绝无声张而又能化为神奇罢了。这自然是指书中宝、钗、黛三者的关系。读者每有把《红楼梦》看作写宝、钗、黛“三角恋爱”,宝钗为“第三者”抢“宝二奶奶”宝座的,固然失之浅薄。但是,宝玉、黛玉为理想情侣,宝钗(有意无意)插足其间;或者说钗、黛双峰对峙而又一体互补,宝玉居间相生(见了姐姐就忘了妹妹),三人纠葛为《红楼梦》一部大书中心,却是不争的事实。《红楼梦》艺术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贾府大家族的背景上写好了这三个人物,写好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第八回下《探宝钗黛玉半含酸》写宝玉正在宝钗处嬉玩:
忽听外面人说:“林姑娘来了。”话犹未了,林黛玉已摇摇的走了进来,一见了宝玉,便笑道:“嗳哟,我来的不巧了!”宝玉等忙起身笑让座,宝钗因笑道:“这话怎么说?”黛玉笑道:“早知道他来,我就不来了。”宝钗道:“我更不解这意。”黛玉笑道:“要来一群都来,要不来一个也不来;今儿他来了,明儿我再来,如此间错开了来着,岂不天天有人来了?也不至于太冷落,也不至于太热闹了。姐姐如何反不解这意思 ?”
这一段描写,特别黛玉所说“间错开了来着”一语,可以使我们感到曹雪芹很懂得用“三极建构”敷衍故事的奥妙。
以上各例表明,“三极建构”的特点是两极主构和第三方作为情节中介的动态的组合。一般说来,这种组合必须并且只能有一个第三者。没有这个第三者,或者多至第四者、第五者,都不能使情节有“恰到好处的复杂性”。但是,第三者必须有一,不能有二,不等于说它只能是一个参与对象。作为中介的第三者可以有两个、三个甚至更多。问题只在于,作家在确定了作为主构的两极之后,把任何其他的人物或方面都作为两极的中介、也就是“第三极”对待,使之始终处于“三”即“参(与)”的地位,就不会有布局散乱的毛病。因此,在得以正确把握和灵活运用的情况下,“三极建构”对于小说的创作有普遍意义。它的实质是一点为中心,两极为主线,第三极为参照。参照乃所以反作用于两极。有参照,两极之主构之关系以至三极之成面才有变化。其在原理上是一分为二,操作上是一分为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三极建构”逻辑上就是这种动态的开放性的组合。它是“天人合一”在小说构思上的投影,一切好的小说故事或简或繁,都是或者可以约简为是这样的组合。因此,作为小说情节结构艺术的基本形式,三极建构是有普遍和永久的意义。
中国古代小说运用“三极建构”的情况各异,有的只在局部,有的贯串全书。熟悉这些小说的读者不难知道,上举各书“三极建构”的组合中,在不降低作品艺术水准的前提下,任何一方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任何一方的艺术生命,都以另外两方的存在为前提,三方既成“鼎足”之势,又在情节的发展中不断调整相互的关系,把情节推向高潮。其运作原理应当就是上述三点成面和三角形稳定性的公理。这些公理在小说艺术上的应用,不嫌生硬地作一类比说明的话,“可以作一个平面”,在文学的意义上就是说“有戏”,或说易于情节的展开。俗云“三个女人一台戏”,就包含这个道理,而“二人转”只是曲艺;“只能作一个平面”,在文学的意义上就是说故事集中于三极的矛盾和斗争,一切超出于三极建构的内容都是多余的;“稳定性”,在文学的意义上就是说只要三极共存,情节就持续发展或处在高潮。而三极的形状、大小和相互间位置关系时时变化,从而形成各种不可预拟之局面。“三极建构”的这三个特点使小说情节有了“恰到好处的复杂性”,如果有一方退出(失败或毁灭),“面”就萎缩为“线”,故事的高潮就将过去,从而只能很快结束全书。例如《三国演义》写诸葛亮(蜀国的支柱和象征)死后,《红楼梦》中黛玉死后,才子佳人小说中“小人”被揭露后……,等等。
其次,是法天之“象”,最突出的是中国古代小说结构的团圆结局和圆形框架。
关于团圆结局,近人多有论列褒贬,不必细说。总而言之,中国古代小说结局几乎没有悲剧,各种末回回目就表明“团圆”的小说书不说,即使从故事发展看硬是不能团圆的情况,作者们也往往要使之“团圆”,众多《红楼梦》的续书是突出的例证。还有《三国》《水浒》《儒林外史》(五十六回本)等书,依其主要故事而言固然是悲剧,但作者总要使正面的人物死后成神或受到封赠,以减少其悲剧的色彩,也可以看出作者企盼团圆的意向。
所谓圆形框架,是指中国古代小说叙事重照应,刻意追求一种往复回环的效果,从而大量作品形成后先呼应、首尾关合的结构样式。如《三国演义》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即毛评所谓“叙三国不自三国始……始之以汉帝。叙三国不自三国终…… 终之以晋国”。《水浒传》始于“洪太尉误走妖魔”,放了“三十六员天罡星,七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单八个魔君”下世,中经第七十一回“石碣天星”的排座次,结于宋江等百零八人死后赐庙成神,末段且有诗曰:“天罡尽已归天界,地煞还应入地中。千古为神皆庙食,万年青史播英雄。”《西游记》结末数列八十一难。《封神演义》结末有封神榜。《女仙外史》结末有“忠臣榜”“烈女榜”。《儒林外史》(五十六回本)起于“百十个小星”降世“维持文运”,结于“幽榜”。《红楼梦》起于青埂峰,结于“青埂峰证了前缘”(见于传抄的靖本第六十七回、七十九回批语),并且前有薄命司名册,后有“情榜”(据脂评)。《镜花缘》前有百花仙子谪世,第四十八回有“花榜”,结于武则天有旨“来岁仍开女试,并命前科众才女重赴红文宴”。《品花宝鉴》起于《曲台花选》的八咏,结于“品花鉴”和“群仙领袖”榜。还有,《金瓶梅》(说散本)起于玉皇庙“西门庆热结十兄弟”,终于永福寺“普静师幻度孝哥儿”,据张竹坡说是 “一部大起结”(第四十九回回评),又说“玉皇庙发源,言人之善恶皆从心出;永福寺收煞,言生我之门死我之户也”(第一百回回评);《醒世姻缘传》的前世因与后世果的对应更是丝毫不爽,等等,故事的结局都可以说回到了它的起点,从大的方面说绝无未了之憾,其结构样式无疑地很像一个“圆”。
显然,世代作家对团圆结局和圆形框架的偏爱和执着不是偶然的,它体现的是华夏民族对世界存在和发展过程为“圆”即“圆满”的理解与企盼。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的渊源不止一端,但在笔者看来,应主要是由于古代的天道观——“天道圆”——的影响。
古代生产力低下,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每停留在感性阶段,故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敕勒歌》所谓“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并且因为寒往暑来、日出月落、昼出夜伏、秋收冬藏等有规律的自然与人事活动,逐渐形成天道循环的观念。《易·说卦》云:“乾为天,为圜。”《吕氏春秋》曰“天道圜”,称天道为“圜道”。“圜”同“圆”,通“环”。“天道圜”即“天道圆”;“圜道”即“圆道”。并且这“圜道”是“圜通周复”“轮转而无废”的循环。即《易·泰·九三》所谓“无往不复”,《老子》所说“(道)周行而不殆”,“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鶡冠子》所谓“环流”,《文子》所谓“轮转”,等等。至周敦颐《太极图》,则径以圆圈中空为“无极而太极之象”。这些从而造成中国人以世界万物发展轨迹为圆为循环的观念,宋儒朱熹就直接说:“今曰一阴一阳,则是所以循环者乃道。”(《朱子语类》卷七十四)所以,以循环为特征的“圆”乃成为中国人思维与表达的心理根据和模拟对象。《易传·系辞上》曰:“蓍之德,圆而神。”张英《聪训斋语》卷上曾明确指出中国人以“圆”为法则的传统:“天体至圆,万物做到极精妙者,无有不圆。圣人之至德,古今之至文、法帖,以至一艺一术,必极圆而后登峰造极。”这应该就是中国古代小说团圆结局和圆形框架的文化渊源。虽然中国古代小说的团圆结局和圆形框架往往要借助释道“转世”“谪世”之说,但从根本上看,释道“转世”“谪世”之说能为中国人所接受,部分地也是由于它至少在形式上近乎“天道圆”,从而仍然显示着古代小说家以“天道圆”的观念把握生活,自觉追求“团圆结局”与“圆形框架”的努力。
所谓“天人感应”,就是说天定人事,人从天命。这个说法虽然也晚至汉儒董仲舒才明确提出,但它的思想内核也早在先秦就存在了。《易传·系辞上》“ 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的话,实际就包含了天人感应的思想。不过,只有到了西汉董仲舒把它提出来加以论证,并得到统治者的提倡以后,这个思想才真正通行社会和深入人心,形成论事为文总要揣测天意、以天命对应人事的思维模式。明代陈献章有《天人之际》诗云:“天人一理通,感应良可畏。千载陨石书,《春秋》所以示。客星犯帝座,他夜因何事?谁谓匹夫微,而能动天地。”这显然是荒诞迷信的东西,但在古代科学不发达的情况下,却是最容易为人接受因而能广为流行的观念,也就很容易成为小说情节构思的基础。而那个时代社会上每天都在大量生产这样的故事传说,也为小说家采为书中的点缀提供了方便,有时甚至成为小说总体构思的基础。
例如《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小说,尽管为了“拥刘反曹”故事有不少虚饰,但是全书基本情节发展仍根据于史实。这就产生一个矛盾:“拥刘”,“刘”未能兴汉一统天下;“反曹”,“曹”却一直居“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并最终代汉自立。对此,作者一委之于“天命”即“炎汉气数已尽”。全书开篇写汉末失政,灵帝建宁年间上苍降下种种灾异,如青蛇堕殿、雌鸡化雄、黑气冲宫……。董仲舒说:“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而惊骇之;惊骇之而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春秋繁露·必仁且知》)显然,这些灾异是上天的“谴告”和“惊骇”,这就使全书笼罩在浓重的“天命论”即“天人感应”的气氛里。接下来黄巾起义、董卓肆虐、曹操擅权,就是“殃咎乃至”了。至“刘玄德三顾草庐”,又重提汉朝的“数”与“命”:
(崔)州平笑曰:“公以定乱为主,虽是仁心,但自古以来,治乱无常。……自高祖斩白蛇起义,诛无道秦,是由乱入治也;至哀、平之世二百年,太平日久,王莽篡逆,又由治而乱;光武中兴,重整基业,复由乱入治;至今二百年,民安已久,故干戈又复四起:此正由治入乱之时,未可猝定也。将军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补缀乾坤,恐不易为,徒费心力耳。岂不闻‘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乎?”玄德曰:“先生所言,诚为高见。但备为汉室之胄,合当匡扶汉室,何敢委之数与命?”
这就可以看出作者置刘备、诸葛亮的努力于与“天命”对立地步的设计。第九十七回《后出师表》诸葛亮曰:“凡事如此,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毛评曰:“虽云非所逆睹,已预知有五丈原之事。”这就是说,诸葛亮乃“知其不可而为之”。至第一百十六回诸葛亮显灵于钟会就直接说“汉祚已衰,天命难违”了。书末《古风》一篇,历数汉兴至三国归晋历史,结末总评也有句云:“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 所以《三国演义》具体描写的主线虽然是“拥刘反曹”,但根本上是“究天人之 际”,终极要说明的是“天命”“天数”与“人事”、人心的关系。其总体构思即诸葛亮在上方谷火烧司马懿不成之后所感叹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所以书中一面浓墨重彩写“谋事在人”,写出三国人物奋发有为的历史主动性;一面写“成事在天”,随时不忘点出“天命”“天数”对世事和人物命运的主宰:凡一人有庆、一事当成、一国当兴,往往有祥瑞;凡一国将帅国君之死、一事之当败、一国之将亡,往往有凶兆。一部书中“天垂象,见吉凶”之描写络绎不绝,俯拾皆是。孤立来看,每处描写似乎只是随意点染的怪诞迷信色彩;联系起来看,实在是作者有意把“天命”作全书的主宰,以“天人感应”为全书“圆形框架”内在联系的表现。
又如,《水浒传》中不仅“洪太尉误走妖魔”是“天数”[],而且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用“石碣天星”坐实百零八人都是天上星宿下世,从而都有一个“神”和“人”的双重身份,形成“天人感应”的格局;另外,全书写宋江等人的命运还有一个九天玄女时时指导和护佑,第四十二回和第八十八回有具体描写。在这两回书中,九天玄女指示宋江过去未来之事,说是“玉帝因为星主(指宋江)魔心未断,道行未完,暂罚下方,不久重登紫府”,这就大幅度地整合了首尾和中间现实部分的描写,实现了全书的“圆形框架”。九天玄女则是这个框架中代表天命而居高临下的人物。从构思的角度,这个人物所起的作用有似于《红楼梦》中的警幻仙子,是不可忽视的。
再如,《封神演义》起于纣王进香,题诗亵渎神灵,女娲以“殷受无道之君,不想修身立德以保天下,今反不畏上天,吟诗亵我,甚是可恶!我想成汤伐桀而王天下,享国六百余年,气数已尽;若不与他个报应,不见我灵感。”于是降下三妖,曰:“成汤望气黯然,当失天下;凤鸣岐山,西周已生圣王。天意已定,气数使 然。你三妖可隐其妖形,托身宫院,惑乱君心;俟武王伐纣,以助成功,不可残害众生。事成之后,使你等亦成正果。”作者引古语云:“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国之将亡,必有妖孳。”很明显,这也是以“天人感应”为基础设定全书“圆形框架”。
还有《红楼梦》的绛珠仙子“还泪”的故事,《儒林外史》“百十个小星”的降世等等,古代长篇说部很少不是以这类天人感应的象征性故事框定全书的,而书中大多今天视为荒诞迷信的情节和细节也在结构上有上下交通的意义。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天人感应”如何结合于“天人同构”的“圜道”观建构并整合全书叙事,形成各具特色的圆形结构,那简直可以称之为“圆体网络系统”。总之,我们可以认为 “天人感应”与“天人同构”一样并且一起,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中国古代小说结构艺术的发展。
“天人合一”思想对古代小说结构艺术的影响是全方位多层面的,读者可以在任何一部用心经营的小说结构中看到它的影痕,并且远不止于上述若干模式。但是,这些模式无疑是此种影响的最突出的方面。它们成为千古小说作家——读者约定俗成反映生活的图式,体现的是中国古人对世界“天人合一”状态的认知与感悟。指出这些结构模式的渊源,从哲学方面说,可以看到“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中国人生活无所不在的深刻性;在文学的意义上,可以成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因为很明显,这些模式的形成和世代沿用,不单纯有形式的意义。形式总包含一定的内容,某种程度上事物的结构特别是它总体结构体现事物的性质。因此,上述各种模式的应用实在又是对作品内容和思想倾向的规范与制约。由此追寻,我们可以对有关古代小说作品的思想内容作新的分析和考量,加深对哲学家与文学、传统文化与古代小说关系的认识。
(原载《齐鲁学刊》1999年第1期)
猜你喜欢
- 悲壮的当山洼之战:伍建章连挑十二位战将突围,罗艺大败杨林扬名(伍建章骂殿连环画)
- 从三流战将到一流勇将的小温侯吕方,斩厉天佑斗石宝的勇将吕方(水浒传小温侯吕方)
- 宋朝版巫蛊之祸:孟皇后触及宫廷禁忌,心思单纯沦为政治牺牲品(巫蛊厌胜之术)
- 家暴婆婆 和太监群乱 这段离不了的婚让公主疯了并惨死?(兖国公主历史记载)
- 春秋权臣赵盾:你眼中那些无能的官二代,可能真的很厉害(赵盾与赵穿的关系)
- 父母陪娃读《史记》之西楚霸王项羽的故事(项羽的故事)
- 文化怪象:一些古汉字,现实中不用,网络上却流行,比如“孨囧”(一穷二白什么意思解释)
- 《辛德勒的名单》-战争中人性的善与恶(辛德勒的名单音乐教案)
- 看懂《论语》你就知道,孔子有三千弟子,为啥他最爱颜回?(子路从而后原文及翻译)
- 《镜·双城》这部剧虐不虐?其实只有男二真岚一人独惨(缘来天注定泰剧小说)
- 搜索
-
- 04-17珍妃卖官败露,被慈禧扒去衣服当众杖刑!最后一句话彻底断送活路(鞭刑)
- 04-17杜贵晨文集(第一卷):文学数理批评(4)(武涉游说韩信)
- 04-17愚人节的来历-来自百度百科(愚人节的来历简介)
- 04-17丁海峰潘长江《武松血战狮子楼》上映,不输经典,堪称最好武松片(武松血战狮子楼演员表)
- 04-17第六次生物大灭绝?美国出现大量生物死亡,科学家暂时不知道原因(虞子期怎么死的)
- 04-17三国时曹魏的五子良将(魏国五子良将 俊)
- 04-17刘邦建立西汉,为什么以“汉”为国号?(西汉地图高清)
- 04-17宋高宗赵构为什么一定要杀岳飞?(赵构怎么逃出来的)
- 04-17中国首创新型动力巨型货轮,能装2万多个集装箱,到底有多牛?(最大货轮发动机有多大)
- 04-17孙莉母女三人晒云之凡造型,各有千秋,粉丝热议不断(云之凡电视剧演员表)
- 1000℃广东塔牌集团股牛初乳什么时候吃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报告摘要_财经
- 1000℃公司起名网免费取名梅州送气哥成粤第500位骨髓捐献者 10年间献血48次_广东
- 1000℃广东冠军杯足球赛举小鬼地球捍卫战行八强抽签|足球|冠军杯|广东
- 1000℃美国调皮皇妃难伺候的一场危机愈演愈烈 只因中国拒做这件事|洋垃圾|视界|危机
- 1000℃百家景区5天迎客947万人次 同比增长16.1%|梅鲍文反应序列关古道|古驿道|雷州
- 999℃呼和浩特球迷巨幅TIFO致敬功勋主www.zzrsks.com.cn帅百场 中国爵爷_中甲_竞技风暴
- 998℃中国大数据版图:东南沿海引领 独角兽扎堆北上深杭|大数据|独嫡一妻角兽|数据_科技
- 998℃小鸣单车作价每辆12元“抵祭天化颜歌债”|小鸣单车|破产_科技
- 997℃ 中国足协公布国家二队集训名单 里皮欲重建男足体系_汪俊林 非诚勿扰江门频道_广东
- 997℃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17年公开招聘应届毕业生结果公示|毕断剑之裔业生|汉族|团员
- 04-16话说三国07 黄巾大起义(将军夫人自称什么)
- 04-16百米空中打造摩天大楼?用钢量高达1万吨,中国如何创造奇迹的?(中国最高的楼房有多少米高)
- 04-16《邹忌讽齐王纳谏》教学后记(邹忌讽齐王纳谏什么意思)
- 04-16《向往的生活6》录制地点疑似已选好,蘑菇屋将设在某美丽渔村(向往的生活在哪里拍的具体地址西双版纳哪个村)
- 04-16太监出身的郑和,为何会被任命为明朝出访各国的“正使”?(郑和下西洋里面的郑和是太监吗)
- 04-16武侠杂谈:因为一个男人,东方不败成了《笑傲江湖》中的强者(笑傲江湖电视剧东方不败结局)
- 04-16What?英国法律里,父母居然不是第一顺位继承人?(英国爵位等级排列英文)
- 04-16百度视频带你看看网播量超21亿的神剧《秀丽江山》有啥玄机(秀丽江山之长歌行 电视剧演员表)
- 04-16神话中的“阎王爷”到底在哪儿办公?(阎王txt完整+番外 百度云)
- 04-16关于英国皇家卫兵,你所不知道的8个独特事实(英国皇家卫队的帽子)
- 标签列表
-
- 历史 (356)
- 不完美妈妈 (181)
- NBA (151)
- 梅州 (144)
- 明朝 (143)
- 我在宫里做厨师 (134)
- 清朝 (127)
- 经济 (97)
- 唐朝 (96)
- 广东 (96)
- 文化 (92)
- 三国 (90)
- 曹操 (87)
- 中甲 (85)
- 政治 (77)
- 汉朝 (75)
- 刘邦 (72)
- 宋朝 (71)
- 刘备 (71)
- 广州 (71)
- 日本 (70)
- 中国历史 (69)
- 秦始皇 (67)
- 康熙 (64)
- 朱元璋 (61)
- 乾隆 (59)
- 唐太宗 (56)
- 诸葛亮 (56)
- 汉武帝 (52)
- 秦朝 (49)
- 英国 (48)
- 市县 (48)
- 史记 (47)
- 读书 (47)
- 春秋战国 (46)
- 武器 (46)
- 梅州市 (46)
- 北宋 (45)
- 跳槽那些事儿 (45)
- 三国演义 (44)